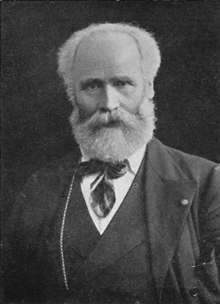前言
第一章 我的临时工生涯
第二章“一场浩劫”
第三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第四章 参加《全红总》
第五章 《全红总》贵州分部
第六章 粉碎邓德礼“政变”
第七章 北京受命
第八章 《全红总》贵州分部成都路小学会议
第九章 首战告捷
第十章 翻印《联合通告》
第十一章 《全红总》云南省指挥部筹备组的成立
第十二章 降服“三司”
第十三章 《全红总》红河分团和大理分团
第十四章 风云突变
第十五章 《全红总》西南区总指挥部西山会议
第十六章 《全红总》专列
第十七章 李炳华和廖荣花
第十八章 我们直观上的“二月逆流”
第十九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的《通告》
第二十章 无耻的叛徒、临时合同工的败类
第二十一章 被捕
第二十二章 在看守所
一 拘留
二 审讯
三 看守的生涯
四 一个面恶心善的好人
五 判刑
第二十三章 在监狱
一 下监
二 “未婚妻”接见
三 记大过一次
四 到基建队
第二十四章 无罪释放:
一 “你翻印《联合通告》,算不算错误?
二 “托《全红总》的福,当然是正式的了。”
三 “我们国家需要健全法制。
前言
本文是方圆先生《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纪念独立工会“全红总”成立三十周年》一文(《北京三春》杂志九七年三、四、五期连载)的补充。本文将以回忆录的方式如实地记录下这一段埋藏在心底三十年的历史。
是耶?非耶?是无法无天的“造反”行为?是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工具,马前卒?还是真正的发生在中国大陆三十年前的自由工人运动?这将留待众多的中外学者和文革研究家们去评述。近几年来,在香港陆续看到不少海外学者对《全红总》的大量评述和肯定,如郑义先生、龚小夏女士、杨小凯先生、杨建利先生等等。
这些学者与笔者素昧平生,除澳洲的方圆先生外,海外的确很少有人知道笔者是《全红总》的直接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这并非是笔者以当年“造反”为耻,被“愚弄”为辱,刻意回避这一段历史,直到有人肯定了,才现身出来。事实上笔者八二年六月到香港定居,九月份,美国伯克来大学的政治系博士,中文名叫胡素姗小姐,一位纯正的金头发美国人,对笔者进行了一次专访,历时一个星期,每天五至六小时。她本来的访问思路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造反派的头头发现自己在文革中身不由已,被愚弄,充当炮灰,整人,最后自己被整的悔恨心理,从而证实大陆官方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一场浩劫。
一开头,我就斩钉截铁地告诉她,我也算是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我们的组织叫《全国红色动者造反总团》,我是这个组织贵州分部的负责人和西南区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我不单被整,而且被判了十年徒刑,坐了七年牢,可是,我们从不后悔。我们不是身不由己,而是身由己,只恨力不及。我们没有被人利用,只是想去利用人,(她追问,想利用谁?我说,利用江青。)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我们确也为中国的广大工人群众争得了可见的、实在的利益,我们虽然都坐了牢,但从没有一个人后悔过。十五年来,我们都引以自豪。
我以为,文化大革命并非是一场浩劫,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就没有如此强烈地对民主的向往和追求,就没西单民主墙运动,就没有现在的改革开放。一席话,使她感到非常惊讶,由于和她预先思考的,听到的,报刊杂志看到的出入太大,她本着一个学者的本能,求知欲的驱使,叫我详细地介绍我们组织的情况。
整整一个星期,在香港亚皆老街离启德机场不远的一栋花园洋房里,我向她介绍了《全红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也谈了周恩来、江青两派强大的势力都想利用《全红总》,可是江青反而被《全红总》利用。最后,由于一个我们至今都不明白的阴谋——周恩来遇刺事件,和北京街头出现落款《全红总》的“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驱使了周江联手(实际上是周在政治局对江施压)提早镇压《全红总》。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江青在接见首都红卫兵时的讲话中提到,她说,我太幼稚了,被一些坏头头所利用。算是检讨,也是总结了她与《全红总》的恩恩怨怨。《全红总》的负责人们都明白,我们的真正对手是周恩来而非刘少奇,而刘少奇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靶子。稍有常识的人也明白,工会,劳动部门,所谓临时合 工制度,这都是国务院的权辖范围,正如别人把周恩来遇刺事件和“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栽脏《全红总》一样,《全红总》的负责人们一开始就确定了把临时合同工制度、工会、劳动部的这些《全红总》首先要冲击的制度和机构集中到死老虎刘少奇身上,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突破口。我可以肯定地说,《全红总》的负责人决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在条件尚未具备的时候,就提出“打倒周恩来”的口号。
我与胡素姗小姐的一个星期的谈话结束时,她感慨地说,你的介绍使我感到新奇,我开始重新思考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从你们的经历看,不象是跟着毛泽东造走资派的反,倒象是我们西方所说的“自由工人运动”。这问题,还尚未完全考虑成熟。不过,你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相信目前在你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海外很难有人认同。比如,我这次到香港准备采访一些大陆人士,香港大学,我的资助机构,就对我提出劝告,只能以大陆官方报刊杂志书籍公开发表的东西为准,如要民间采访,他们不予资助。所以,这间小房,都是我自己出钱租借的。另外,你可能不知道,按我们的规定,我将付给被采访者每小时谈话十六元港币的酬金,听了你的谈话,我觉得,我付给你钱,对你是一种侮辱,但我应该向你说清楚。最后,她征求我的意见,我们的谈话能否发表?我告诉她,我要随时进出中国大陆,立志从事大陆的民主运动,因此,不能发表,不能公开我的身份,但可以在她的著作中引用。想不到,事隔十五年,倒是我自己食言,公开发表。但愿四这篇文章胡素姗小姐能看到,唤起十五年前的回忆。
除此之外,一九八六年初,我向当时中国民联的主席王炳章先生汇报筹组中国民联贵州分部的工作时,也简介过自己的经历,谈过自己在文革中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贵州分部和西南区总指挥部的负责人。当时,海外不少民运人士正在互相指责,谁在文革中当过“造反派”,是乎以此为耻。有人还指责王炳章也参加过造反派。一九八九年三月,当中国民联重庆支部被重庆当局镇压事件公开见报后,当时以胡平主席为首的中国民联总部尚不了解详情,因为上任主席王炳章及副主席柯立思未移交此份档案。我接总部监委主任薛伟(当时叫黄世忠)的通知,叫我向总部汇报中国民联重庆支部从成立到被破获三年来的工作情况。在汇报中,我也简介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是《全红总》贵州分部及西南区总指挥部负责人。这篇汇报材料想来胡平先生,于大海先生和薛伟先生都已看过,应该有所记忆。
现在,既然方圆先生,即是当时《全红总》总部的五人核心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周牧先生在其介绍《全红总》的文章中已将我在《全红总》的身份公开出来,作为《全红总》的直接参与者、策划者、领导者之一,我有必要,有责任将我曾经热爱过,为之奋斗过和贡献出青春的这一组织的真实历史公诸于世,以供自由工人运动的参与者和海外学者研究。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许对目前正在从事中国的民主运动和自由工人运动的精英们,能有所借鉴。
第一章 我的临时工生涯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与《全红总》的创建者、领导者方圆(原名郑天赐)自幼相识,因为父辈是世交,都是国军的高级将领。但我们并非是共产党的天生反对者,血管里也并没有从生下来就流着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血液。我们勤奋读书,自幼就想把自己的一生和才智贡献给祖国,让祖国繁荣富强。但由于考虑到自身的天生弱点,家庭出身不好,都有意识地放弃“文史哲”而主攻“数理化”。也许,这也叫做自觉地“退避三舍”吧。
1963年,我在贵阳七中高中毕业,当时正值62年所谓的“蒋匪窜犯大陆”,全国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路线,唯成份论的思想主导一切,高教部内部有通知,对于黑五类的子弟,“准考不准取”。此条路线贯彻到66年文革开始,又被那些高干子弟,首都红卫兵“一司”“二司”及“联动”的革命小将们发扬光大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我的高考成绩,六科平均是81.4分,全校第二名,得到的却是不录取通知书。第一名沈利晖,我的同窗同桌好友,82分,录取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雷达系,第三名劳远英,74分,四川大学,第四名,魏美铭(女),70分,不录取,其父是国民党八十九军副军长兼三二八师师长,系郑天赐(方圆)父亲旧部,当时寄住郑天赐(方圆)家中。倒数第一名伍衡德,34分,贵州农学院,父母都是共产党员。
其实,我报考的不过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建筑系而已。第一志愿清华大学物理专业,只是我的物理老师高言赢一定要我填的,我是连续五年的物理科代表,物理科成绩最为优秀。读北大、清华,这些名校,可是我们这些黑崽子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家庭出身不好,从小就养成了与人无争的自卑感,对那些家庭出身好,尤其是共产党员的子弟,心里总让着几分。我总认为,搞建筑,真正地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共产党总该放心我吧。当我接到不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哭了,我是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一次打击。我的物理老师高言赢,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也陪着我哭了:“我手下的物理科代表,没有一个不考上重点大学的,想不到,他们连一个普通大学都不让你读。”
他的哭,除了同情我之外,也许是自身有感而发。那年代,阶级路线的贯彻已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他是地主出身,外表冷漠,自视清高,与人无争,但教书却是一流。教我们政治的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教师,名叫沈慈恩,共产党员,同样是清高冷漠,这两个看来不可能走在一起的人,不知怎么搞的,恋爱了,他们深深地爱着对方,那年头,谈恋爱也得看家庭出身。沈慈恩因为是党员,先向学校党总支申请要与高言赢结婚,党组织对她发出警告,要她站稳阶级立场,与高言赢断绝关系,否则要受到党纪处分。沈慈恩不听警告,一再申请,党组织决不批准。最后,沈慈恩写出了退党申请,党组织给予了她开除党籍的答复。她并不悲伤,因为得到了自由,可以和高言赢登记结婚了。